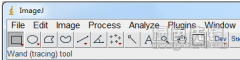|
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体)是否是“服务型社会”或者是否处于“服务经济时代”,必须要综合考量,至少要综合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这两个指标。 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崛起改变了需求结构,文化精神等服务需求快速提升。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到2016年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8472元上升到2018年39251元的水平,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以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上升到2018年的14617元,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0%以上。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迅速崛起。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预计到2022年将增至6.3亿,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和全国人口数量的45%。中等收入群体拥有稳定的收入和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条件,对追求高品质生活有着强烈欲望,也愿意为优质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因此,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的消费能力、文化精神领域的消费欲望以及日益增大的群体规模,将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从恩格尔系数来看,自199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0.1%下降到2018年的2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8.6%下降到2018年的30.1%。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最初的基本物质需要转为更高层次的需要,城乡居民家庭的服务消费占比逐年提升,每年约提高0.8个百分点,占消费总支出的1/3强。目前,消费者用于自身发展、休闲享受型服务消费的比重、内容方式不断增多,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进入服务消费阶段,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日益呈现碎片化、个性化和体验化趋势。消费者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及消费体验,体现在消费支出上就是用于医疗美容、文化旅游、休闲******和体育健身领域的支出逐渐增加。 二是制造业强国建设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互促共进”,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找到了新思路、新路径,更是抓住了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的“牛鼻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从发达国家产业演变历史看,从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柔性化生产模式取代福特制生产模式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日趋突显,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地位开始不断提升,制造业外购从制造业内部分化的或从市场内生发展来的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并且在产品消费中还要消费大量的互补性服务,以提升自身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争取更大的价值。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整个服务业产值的70%。世界500强企业中,56%的企业从事服务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稳居世界制造业大国之首,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偏重于组装和制造环节,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价值链上游(如研发设计)和下游(如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高端环节仍被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嵌入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并向生产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
热门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