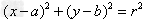|
国家何时能在强大利益集团的反对下执行政策?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已经考察了能力的官僚来源,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具有类似官僚能力水平的国家在目标实现上会有差异。我们引入了国家战略能力的概念来解释这一难题。它指的是国家为追求政策目标而动员或调动利益集团的能力。我们确定了国家用来对抗反对派的四种一般类型的战略:招募盟友、调整利益、限制接触和使利益集团静默。我们在加州、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气候和清洁能源政策制定案例中研究了这些策略。气候政治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分配性政治领域,有着来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国家战略能力的概念是对官僚能力概念的补充,以显示国家如何积极组织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以推进政策目标。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引入了战略国家能力的概念,以拓宽我们对官僚自主性之外的国家能力的理解,并推动最近重新评估先进工业化国家国家能力的努力. 该学科缺乏与国家能力的战略来源的接触,这使得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能够反对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在其他情况下却不能追求国家目标,即使官僚能力没有变化。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先进工业化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国家行为者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进行战略互动,试图根据国家目标动员和解散利益集团。我们确定了针对有组织利益的四种一般国家战略——招募盟友、限制准入、调整利益和压制利益——并讨论了政策制定者应用这些战略的一系列工具。 我们的论点对有关利益集团中介的辩论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它挑战了多元化国家仅仅是利益集团竞争的观点。虽然多元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不一定像社团主义环境中那样与利益集团进行长期谈判,但它仍然积极参与管理利益集团的准入和偏好。美国的电动汽车政策案例和加州的授权案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协调的制度中,国家可能并不总是被束缚在长期利益中介的刚性制度结构中。正如德国煤炭委员会的案例所反映的那样,它在复制和改变这些论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就法国而言,政府没有寻求协商一致的谈判,而是与部分汽车工业站在一起,发出了向电动汽车长期转变的信号。 我们建议进一步研究四个核心问题,其中三个与国家战略的来源、选择和有效性有关。首先,如何解释战略能力的差异?如上所述,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可能会导致政治参与者和国家之间战略能力的差异。对政策企业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来检查个人层面的特征,包括学习过程。国家能力的组织来源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官僚能力。我们要明确的是,官僚自治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总是充分条件。我们假设官僚和战略国家能力可能有些相关:更大的专业官僚机构可能具有对利益集团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力。但我们也发现,在具有高官僚能力的司法管辖区之间,战略国家能力存在差异。例如,加州成功实施了上文讨论的 2020 年气候目标,而德国尽管有类似的主管环境机构,但未能实现其 2020 年目标,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德国并未将决策过程与有组织的利益隔离开来。一些与官僚能力无关的组织特征可能很重要。例如,政治任命者与职业官僚的比例可能会通过塑造组织的知识和网络来影响战略能力。同样,机构的声誉可能会影响他们动员利益集团的程度。综上所述,这表明未来对战略能力来源的研究将有助于判断战略能力是否倾向于与官僚能力共存,或者是否可以替代它。 其次,如果决策者可以选择多种策略来实现同一目标,那么如何解释策略选择?我们在上面提出,成本和制度都可能很重要。例如,通过补偿来平息利益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效但代价高昂的策略。高预算支出可能会为政策制定者追求相互竞争的目标带来权衡。至于制度,我们的案例来自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政治体系,以表明战略性国家能力在多种制度环境中很重要。但我们还不知道国内制度如何促成或限制某些类型的国家战略相对于利益集团。例如,在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表现出高度协调的民主国家中,补偿可能是一种更有可能的策略。长期的讨价还价关系有利于政策失败者的补偿。此外,在高度协调的机构环境中增加信息流动可能会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同时,在具有协调或合作主义利益中介的环境中,限制访问可能不是一种选择。除了利益集团中介之外,法律制度还可以限制策略的使用。将政策设计委托给官僚机构——一种限制准入的重要工具——可能面临法律约束。司法管辖区在法律允许将大量权力下放给官僚机构的程度上各不相同(在具有协调或法团主义利益中介的环境中,限制访问可能不是一种选择。除了利益集团中介之外,法律制度还可以限制策略的使用。 第三,不同策略的效果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国家战略能力如何与政治和政策结果相关联至关重要。同样,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它特别指出战略本身的特征和政治机会结构作为解释因素。例如,有组织的利益如何集中或分散以及统一或分裂的程度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者动员或解散利益集团的机会。 第四,关于官僚国家能力的研究提出了对强国的规范性影响的质疑,这对战略性国家能力也很重要。虽然此类辩论在历史上一直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腐败政权中的自治国家,但我们承认,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当官僚和立法者以不民主和腐败的方式行事时,更多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是不可取的。限制访问的策略最有可能与民主问责发生冲突,尽管这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案例表明,立法机关将政策设计委托给自治机构限制了利益集团接触立法者的机会,但通过 CARB 的正式磋商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参与空间。这可能使一系列利益集团有更平等的机会,独立于他们通过竞选资金寻求接触立法者的能力。 正如 OECD 国家 25 年实施气候政策斗争的好坏参半的记录所反映的那样,国家能力对于政策实施至关重要。更一般地说,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问题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变得更加紧迫。除了气候变化,中国国家主导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政策反应已经开始重塑富裕民主国家的国家行为。许多过去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上。因此,在一个新的国家干预时代,重新评估先进工业化国家国家能力的来源——制度和战略——是一项重要的努力。 |
热门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