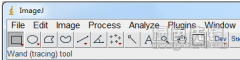|
多宝塔高33米,12层。“最初在木板上走动时,脚手架会晃动,这对普遍恐高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黄能迁回忆,“但是,当工作进展到收尾阶段时,竟然有同事可以在木板上如履平地,甚至‘上蹿下跳’。” 在此之前的3月至4月,该团队完成了多宝塔塔内龛像及铭文的调查记录。“塔内有近80个龛,大大小小的造像不计其数。”黄能迁说,他们要对每一个龛的高、宽、深等数据进行采集,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从头到脚的记录,头冠、面相、服饰、手势、坐姿等细节描述一点也不能少。 “有的造像仅有二三十厘米高,我们便把钢卷尺夹断,便于测量。”邓启兵说,在光线阴暗、空间逼仄、布满灰尘的塔内,需要开着LED照明灯,小心翼翼地观察和记录。 工作人员还采用先进的测绘拍摄技术——多基线D扫描技术对龛窟进行拍摄扫描,采集数据。据介绍,一个龛窟要拍摄几百张甚至上千张图片,才能采集到完整的数据。 以书中呈现的大足北山第245号龛——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为例,这个晚唐最为精美的石龛艺术作品,其测绘图的数据采集来自1000多张图片,然后由两名工作人员绘制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为便于读者查阅,《大足石刻》第一至八卷图、文分册编纂。如果说考古调查组是在给造像办理“身份证”的话,那么摄影组则要为造像拍“登记照”。 郭宜说,拍摄图片受天气制约很大,“光线柔和的时候才能拍摄,有时为了等适宜的光线,在脚手架上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2015年夏天,在拍摄宝顶山大佛湾圆觉洞洞底时,重庆出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郑文武攀爬至洞顶天窗进行拍摄。他正拍得入神时,忽然感到身上奇痒无比。他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掀起衣服,只见浑身爬满蚂蚁。“那一刻,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眼见就下暴雨了,我只有忍着继续拍摄。”回忆起那一幕,至今他仍心有余悸。 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王怀龙告诉记者:“《大足石刻》共涉及到600多个龛窟,每个龛窟中的造像都要用文字、测绘图、拓片、摄影图片忠实记录,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2004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曾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办“石窟寺考古培训班”,刘贤高、邓启兵、黄能迁等课题组成员现场聆听了先生教诲。“使劲看,看明白。”先生的“六字箴言”令他们铭记于心。 “各地石窟都具有特殊性,这使得已有标准和规范缺乏普适性。”黎方银说,这时,大足石刻研究院总会邀请马世长等专家前来指导,“马先生和蔼可亲、不求回报,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记录、如何整理。” “2011年,我曾赴北京拜访马先生,临走时,他从沙发上拄着拐杖艰难地站起来,笑着对我说,回去告诉黎院长,我身体好着呢!”黄能迁回忆道。 马世长患病后,向黎方银推荐丁明夷担任《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主任。黎方银和丁明夷是忘年之交,当得知重庆在编纂《大足石刻》一书时,丁明夷感叹道:“你们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 2018年2月,马世长、丁明夷的恩师宿白与世长辞。“石窟考古界人尽皆知的是,宿先生有一个未了的心愿——见证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编纂完成一部大型石窟考古报告。”黎方银说,先生的心愿终于在大足实现了。 《大足石刻》中也铭记了先贤的贡献。其中的第十卷为历史图版卷,这一卷收录了1940年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以及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所拍照片等珍贵历史影像。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考察团成员们论断:大足石刻“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实与敦煌相伯仲”。 “一位又一位学人,一代又一代先贤,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其信仰般的力量,不断延续着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不断传递着大足石刻的人文光辉。”黎方银说,70余年前的历史影像和一代代大家为大足石刻付出的心血,体现在《大足石刻》的字里行间,永世流传。 |
热门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