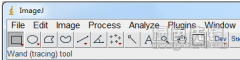|
其实何止一个章家敦。2016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ing Chinese Crackup”(中国即将崩溃),他后来辩解说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标题那么醒目,文章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不是几句辩解可以打发的。 到了2017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对夫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崩而不溃》。女的原来是记者,叫何清涟;男的曾在体改部门工作过,叫程晓农。我一直读不懂这个书名,崩了怎么会不溃呢?他们似乎想说中国要崩溃,但又没有多大把握,为了显得不那么离谱,所以弄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书名。 2018年,美国著名杂志《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煞有其事地问道,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2018年稍晚一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叫“The Land Failed to Fail”,意思是中国应该失败但是结果它没有失败。这个标题透露出一种极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人很肯定地认为中国的那种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功,一直等着中国崩溃,等了70年,到现在还贼心不死。 以上的例证让我们看到,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一定会碰的头破血流;但是胡老师刚才从十四个方面点用大量的证据说明这些人说的全是错误的。 问题是为什么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有人会一条道走到黑呢?这涉及到预测背后的理论依据。西方的确有一整套理论,它使得很多人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道路肯定走得通,就是所谓的西方道路,其它的道路肯定行不通,包括中国道路。 这些理论五花八门、不仅相同、层出不穷。这方面的书实在太多、太多了,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点,看看他们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它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自己所走的道路。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这本书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获得若干个图书奖。该书的重点是第三部分,“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作者说,“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二十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 与这本书相似的是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 1981年出版的《欧洲的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经常听说,日本奇迹、东亚奇迹、中国奇迹,但此前欧美已有人大谈欧洲的奇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不用详细介绍,因为后来有其他学者评论这本书说,它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甚至“文化种族主义”的色彩。 在过去20多年,这一类的书也大行其道。1997年,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出版了《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有中译本。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它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很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性,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问题是,中国今天依然很大,很统一,不是照样发展起来了吗?这套理论解释得了吗? |
热门关键词: